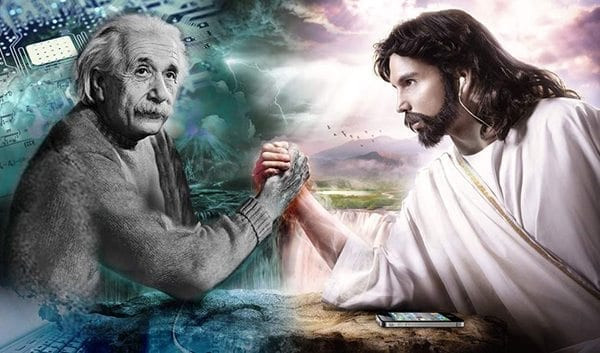自從歐洲「啟蒙時代」以來,到了20世紀中葉,可說是「科學主義」的盛期,許多人認為科學是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途徑。所謂「科學主義」就是一種對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的極端信奉或推崇,就如物理學家拉塞福爵士(Sir Rutherford)所說的:「除物理學之外,其他皆是集郵(Stamp-Collecting)。」當代著名哲學家、杜克大學教授亞歷山大‧羅森堡博士(Alexander Rosenberg)也同樣強調,只有科學方法和科學證據,才是確定真理的唯一途徑,其他形式的知識或信仰都是次要,而且是不可靠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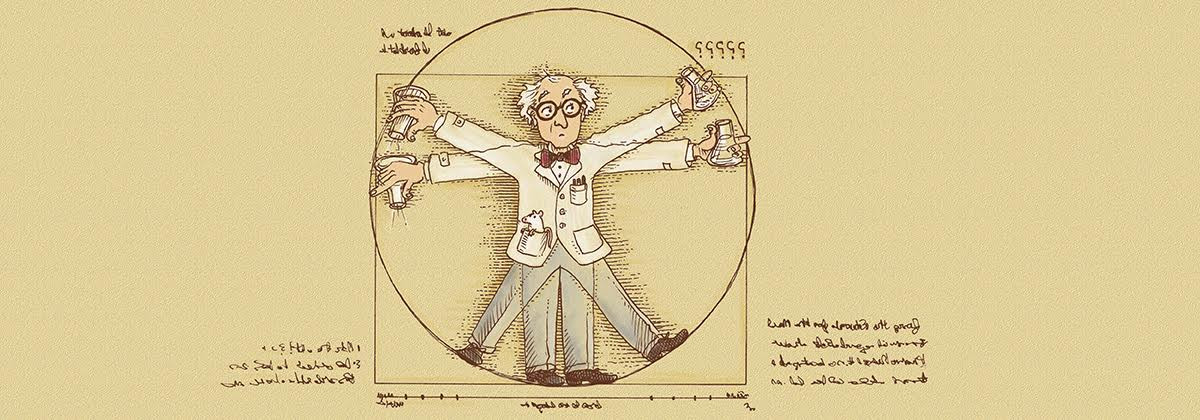
不斷推演
這些人的結論顯然不是用科學方法可以得到的,那麼我們怎麼知道他的結論是不是正確的呢?這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「準則問題(Criterion Problem)」。就是說,我們怎麼知道某種方法是「正確」的呢?我們必須要能用其他的方法來證明這方法是正確的才行(自圓其說是不夠的);然而我們怎麼知道那個「其他的方法」是正確的呢?於是只好沒有止盡地推演下去。
換句話說,測試一個「認知方法」是否真確無誤,就是當我們用這「認知方法」可以從一個已知的「錯誤」命題,利用這「認知方法」得出那是個「錯誤」的答案;而從一個「正確」的命題,可以得知那是「正確」命題的答案;於是我們可以信任這「認知方法」是可靠的。
所以為要測試這「認知方法」是否可靠,我們必須要預先知道一些不用這「認知方法」而有的「正確命題」才行。那麼我們又怎麼會知道那「正確」的命題是「正確」的呢?這就是「準則問題」帶來的麻煩。所以我們至終只能「相信」這「認知方法」是可靠的才行。
科學建立在信心上
這是一種有理由但是不能證明的「信心」,知識是源於這種信心的,科學也是建立在這種「信心」上的。
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上述的概念。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因「烏台詩案」被貶至黃州時,曾填了一首有名的《水龍吟》:「不恨此花飛盡,恨西園、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,遺蹤何在?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,二分塵土,一分流水。細看來,不是楊花,點點是離人淚」。對其中的「一池萍碎」句,蘇東坡自註道:「楊花落水為浮萍,驗之信然」——他說楊花(柳絮)掉落池塘水面後,隔夜就會化成浮萍,他用錯誤的方法去檢驗這現象,認定是真的、是可信的(「信然」)。他用了「觀察」的方法「驗之」,得到的結論卻是錯誤的(事實上楊花落水不會成為浮萍),除非他有別的辦法知道楊花能不能化為浮萍,否則他就不能知道他的「驗之」的方法是不可靠的。
這種「科學主義」的哲學觀點,雖有部分實用的立場,但是不難看見其中許多的限制、許多不能有效測量的現象,比方「愛情」、「價值」、「倫理」、「善惡」等等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問題,都不是「科學主義」可以回答的。不但如此,用科學方法也不能得到所有意義的答案。
比方說:若問在火爐上的這壺水為什麼沸騰?我們用科學方法可以說:一、因為壺裡水的溫度達到了攝氏100度;二、由於熱量從爐火傳進水壺,壺裡水分子的動能增加,導致其「蒸汽壓」達到並超過水面的大氣壓,於是水從其「液態相」吸收了「潛熱」轉化為「氣態相」,造成沸騰現象(這個解釋是從物理的視角,是更正確的,但是並不見得是這壺水會沸騰的所有原因);三、這壺水之所以會沸騰,是因為我想要泡杯茶來喝(這是另一種不同的解釋,是從「目的」的觀點出發的)。
我們可以說,物理的了解不是這壺水會開的原因,而是「水怎麼會開」的過程,所以若要了解這壺水「為什麼」會開,從物理學而來的答案可以甚至是全然「文不對題」的。同樣,若要問自然界為什麼存在這裡,「大爆炸」論不但不見得正確,也更不見得是最合適的解釋。許多「為什麼」的答案,都不是科學可以回答的。
科學、宗教不可分
科學與宗教都應該是尋求真理的途徑。用科學方法,我們可以有效地分辨出什麼是錯誤的(證偽),但是真理總是需要用信心來獲得的。真實的信心是需要有適當的理由來支持的,因為信心固然可以讓我們認識真理,但信心也可能是錯的。這是信心的本質,科學主義與宗教都是信心的立場,科學方法只是獲得知識的方法之一。愛因斯坦說:「沒有宗教的科學是殘缺的,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」。信哉斯言!
科學與信仰|黃小石By accepting you will be accessing a service provided by a third-party external to https://cchc-herald.org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