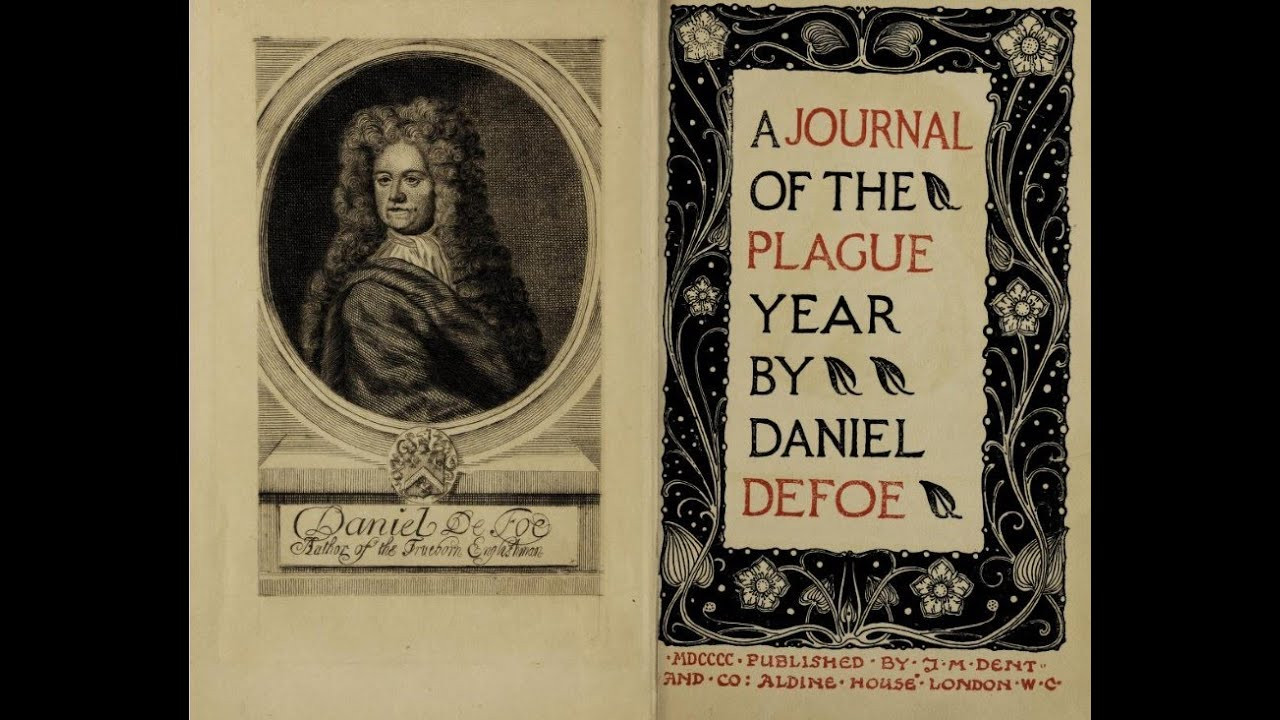面對21世紀迄今最嚴重瘟疫,華文作家的封城日記在海外出版令輿情嘩然。此時重溫18世紀初的《大疫年日記(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)》,不由為當年的英國君主與人民所具有的覺悟鼓掌——他們沒把作家笛福(Daniel Defoe)打成賣國賊,反首先在境內出版這部外揚家醜之作。
被人揭下面具是失敗,自己揭下面具卻是勝利。
《大疫年日記》相較於小說更接近紀實文學,透過深度資料研究、採集豐富回憶與軼聞以及常被忽略的人性故事,記錄英國歷史上最後一場讓倫敦人痛不欲生的腺鼠疫慘況。讀者將書中引用的統計數字、圖表、政府公告視為信史,就連社會學家和傳染病學家也以之為信息源。
有人以為這本日記是在逃過1666年的倫敦大火之後輾轉到讀者手上,其實倫敦瘟疫之年笛福只五歲,《大疫年日記》成書之時則距災難半個世紀。世人既已走出陰影,何必再揭傷疤?只因1720年,法國馬賽又爆發了鼠疫!笛福藉敘述人H.F.表明:作為倖存者,要以親身經歷寫下「備忘錄」,好給後來的人免於重蹈覆轍提供借鑒!
未曾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。
人不了解歷史,就像不知道自己是樹的一部分的葉子,無從明白前途。《大疫年日記》以全景式視野,還原倫敦97個教區的疫情;又藉編年體,串聯起從1664年9月到1665年終,瘟疫發端、高峰、終結的承轉跌宕。即使300年後身處新冠病毒特大流行的今人,讀來仍不違和,甚而產生共鳴:
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,在街上行走或在集市裡購物時,突然倒斃」;「市政當局製定嚴格法規,將染上瘟病的房屋強行關閉起來,事實上常常是將有病的人和沒病的人關在同一個屋子裡,造成出乎預料的悲慘後果」;「隨著傳染病愈演愈烈,有些教區的運屍車幾乎通宵奔忙」......
沒有哪一次巨大的災難不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。
這進步需要一個前提:清楚明白災難的教訓。故真正的生活悲劇不是遭受了多少苦難,而是當不起那苦難!我因而同意這樣的說法:即使是一場大災難,只要有勇氣如實記錄下來,也會具有史詩般的恢弘氣度。這不需要抓起槍打死敵人的勇氣,也不需要挑戰騎著白馬的死神的勇氣,單單需要超越國族黨政之狹隘而獨立思想和表達的勇氣。
同樣是著名英國人的邱吉爾(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)說:人可以向後看到多遠,就可能向前看得更遠。笛福顯然是看得更遠的人,並將倖存者的自覺化為《大疫年日記》警示時代:「如果有人因此情景而默默流淚,甚而至於相信世界末日的預言,這是一點不奇怪的。要是他們知道這場大規模的傳染病結束之後的次年,倫敦還會發生大火災,將這個城市的四分之三夷為平地,他們大概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審判已經降臨......」
於墮落的世界充當上帝懲治和賜福的見證人。
「災難的見證者,有責任揭示災難對人性的摧殘和扭曲,因為這才是災難所造成的最大災難;見證者也需要讓人保持活下去的信念,不是苟活而是盡可能有意義、有良知地活下去。」這是笛福的使命,也是一切自覺人類同處命運共同體之人的探索。如作家方方,也以自己的日記繼續著倖存者的責任:「在悲傷和抑鬱的併發症下,對未來沒有確定的感覺,容易導致內心高度地缺乏安全感;在自己抓握不著,無法掌控的情況下,會導致最基本的安全感喪失;這時要尋找點什麼讓自己踏實?」
笛福是讓H.F.把性命託付給上帝,於墮落的世界充當上帝懲治和賜福的見證人:「多半時候都在深深感謝上天保我全戶人平安,不斷招認自己的罪行,每天都向上帝悔罪,透過齋戒、自罪及沉思向上帝祈求......」在孤立無援中依靠信仰度日,讓既無主角也無情節的《大疫年日記》更具感染力,因為那是倖存者走向新生的唯一有效方法。
生死之間,由百分比勾勒出界河。
現在,新冠病毒令187個國家和地區染疫。誰還能說這只關乎一地一方?在方方筆下,「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,關你幾天不讓出門,或者進社區必須通行證。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以前每月用一本,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;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,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,且有棺材,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,一車摞上幾個,一併拖走;災難是家裡不是一個人死,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......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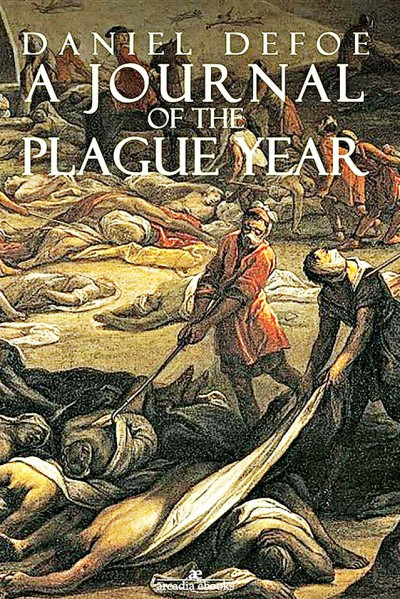
全球疫區死亡率各異,卻都是無情的生死界河。倖存者,就是僥倖活下來的人。每一個倖存者的生,都以罹難者的死為代價。大難不死活下去,就當承擔一種道義責任:帶著罹難者的希望,找出災難的起因,避免悲劇重演......
這個想法讓我恍然大悟,古往今來的傳教士、宣教士,豈不是以倖存者情懷——擺脫了在罪中永死之悲慘宿命的感激之心,前仆後繼地奔向蠻荒之地?救命之恩唯救人方報,正如倖存者之責必使人倖存方盡。
By accepting you will be accessing a service provided by a third-party external to https://cchc-herald.org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