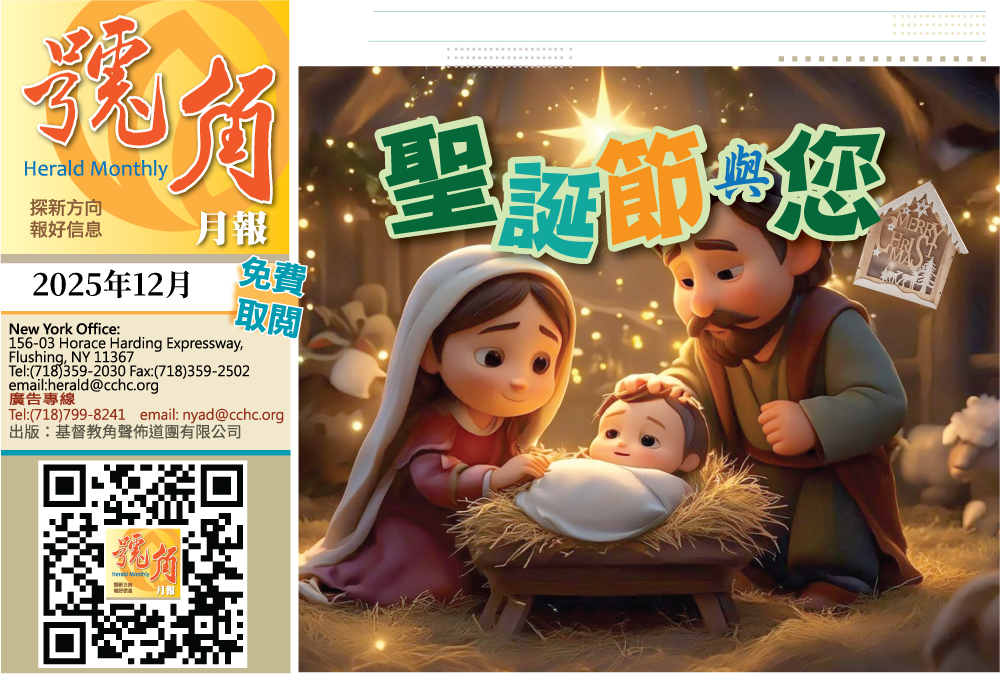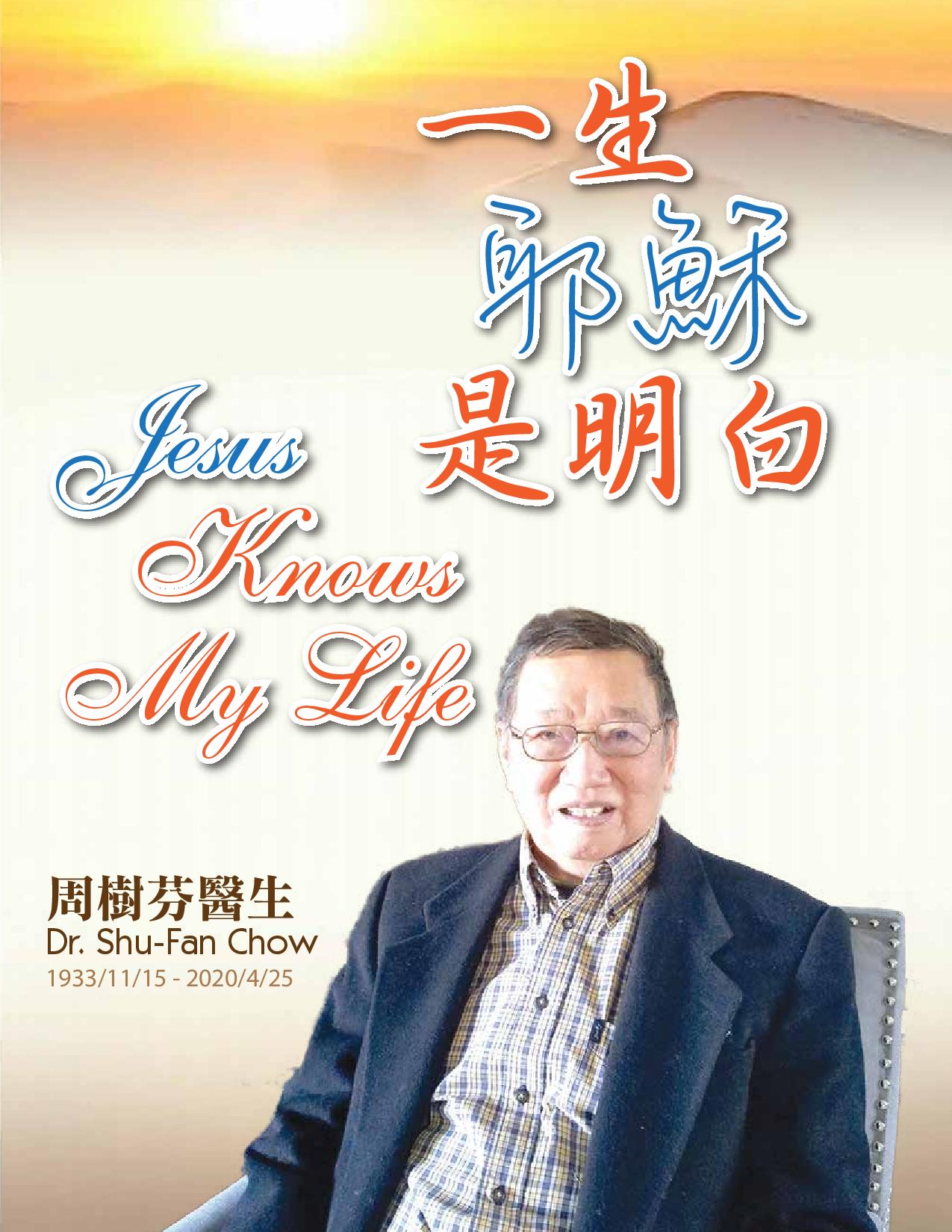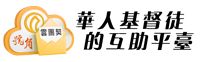基本信息
詳細內容
近來,關於蔡依林演唱會的討論,在網絡上悄然發酵,並逐漸轉為一場情緒濃烈的爭議。焦點並不在歌唱技巧或舞台完成度,而是那一整套令人不安的視覺語言——巨型蟒蛇盤踞舞台、巨型公牛低伏如獸、第三隻眼凝視觀眾、混種動物游走其間、「七宗罪」被逐一點名。有人說,那不像一場演唱會,更像一座被點亮的祭壇,空氣中瀰漫著獻祭般的張力。

於是,有人在論壇與社群中直言不諱,用「撒旦象徵符號」「撒旦化」「像邪教儀式」來形容這些畫面,甚至進一步把歌詞與拉維式撒旦教所強調的價值——自我崇拜、慾望至上、顛覆傳統道德——連結起來,彷彿在那片舞台背後,潛伏著一套更深層的世界觀。

但若細究這些指控的來源,會發現它們多半不是來自嚴密的神學論證或藝術分析,而是來自一種更原始、也更脆弱的地方:個人的靈性感受。有人說氣場不對勁,有人說心裡發涼,有人甚至形容看完之後,身體出現莫名的不適。那不是理性推導出的結論,而是一種被觸動後的反射——彷彿某些畫面,正好碰觸了人心深處尚未結痂的傷口。
其實,舞台上的黑暗之所以令人恐懼,並不是因為它陌生,而是因為它太熟悉了。
恐懼、創傷、罪疚、對死亡的無聲逼近、以及在人群中仍然無處安放的孤獨——這些不是藝術家憑空創造的符號,而是早已沉積在無數人心底的真實重量。只是平日裡,它們被工作、娛樂、社交與笑聲層層覆蓋;直到藝術把它們放大、拉近、逼到眼前,人便突然無法逃避,只能感到刺痛。
那是一種被照見卻尚未被醫治的痛。
是一種「我知道這是我,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」的痛。
於是黑暗在舞台上顯得如此濃稠:蛇象徵纏繞的恐懼,獸象徵失控的本能,第三隻眼像是人內心那雙無法閉上的自省之眼,日夜審判自己;七宗罪不只是神學名詞,而是無數人反覆跌入、卻又無力掙脫的循環。這些畫面之所以讓人不安,正因為它們不像寓言,更像鏡子。

然而,問題不在於黑暗被呈現,而在於人是否被留在黑暗裡。
藝術能誠實地揭開傷口,卻無法為人縫合;能讓人承認破碎,卻無法使人重生。若黑暗只是被反覆凝視、被美學化、被合理化,人終究只能學會與痛共存,而不是得著釋放。

聖經對此並不天真。它從不假裝人性光明無瑕,也不回避最深的陰影。十字架本身,就是歷史中最黑暗的時刻——羞辱、背叛、暴力、死亡,全然攤開。但關鍵在於,那黑暗並沒有被奉為終極真理。正是在最深的暗處,真光進入世界。耶穌說:「我是世界的光,跟從我的,就不在黑暗裡走,必要得著生命的光。」(約翰福音 8:12)
因此,當我們觀看那些充滿黑暗密度的舞台時,真正需要分辨的,不是某一個符號是否「夠不夠邪」,而是:這些黑暗,是否指向一條出路?若沒有光,黑暗只會加深人的疲憊;但若黑暗成為背景,光才顯得真實而必要。
或許,這正是這些網絡爭議背後,更深層、卻未被說出口的集體呼聲——在人被允許誠實面對恐懼、創傷與罪疚之後,仍然渴望一種不屬於舞台、不屬於符號、不屬於任何人手所造的光,一種能穿透痛感、進入人心,使人不只是被理解,而是真正得釋放、得醫治的真光。
本文純屬作者觀點,不代表角聲佈道團立場與發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