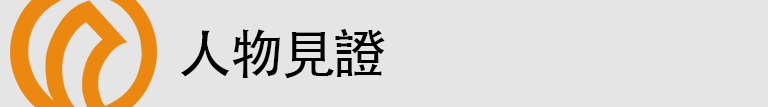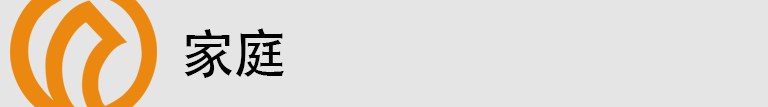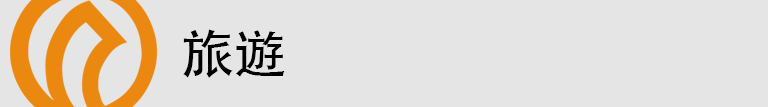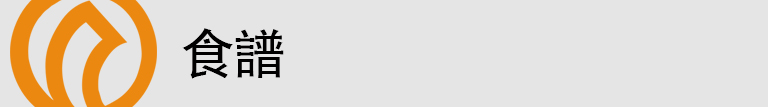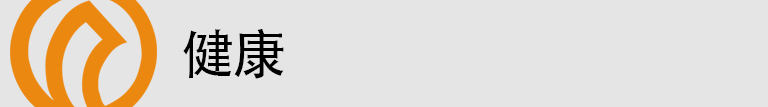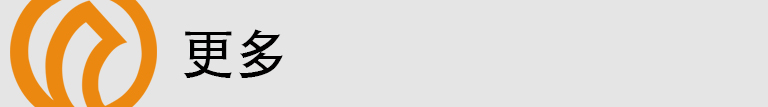2019年7月
映霞
常常有朋友問我為什麼老喜歡去巴黎,我總是會毫不猶豫地回答:「巴黎有我的一切,包括影響我思想成長的人。」
四年前,妹妹的女兒Vivian初中畢業,我想帶她去見見世面,所以又一次來到了巴黎。
有一天,我們橫跨塞納河上的阿爾瑪橋往左岸走,來到橋南端左側的抵抗廣場,在靠近河岸的一個角落拾階而下後,一個巴黎下水道的鐵柵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。
時空的裂痕中,一個影像突然無故的在鐵柵欄後跳出,凝固在我的面前,我無意識隨口說出了一個名字:冉阿讓。
誰是冉阿讓
「誰是冉阿讓?冉阿讓在哪?」Vivian看看我喃喃自語的樣子,詫異地問我。
過了一會兒,看著仍然沉默不語的我,她又說:「和我說說冉阿讓吧!」
那是雨果的冉阿讓,還有他身上背負著的始終昏迷不醒的馬里斯,他們正從深深靜謐的,是絕對靜謐的,黑夜的巴黎下水道裡爬出來。
凡是看過雨果《悲慘世界》的人,一定都還記得這樣的情節:年歲不輕的冉阿讓,背著巴黎起義巷戰中負傷的青年馬里斯,在巴黎的下水道中踉踉蹌蹌地行走,躲避著警官沙威的追捕……
這一章節一直緊黏在我的腦袋裡,縈繞,直到那個時刻,《悲慘世界》所有的故事情節又再次顯現……
「佈道」小說
這是一部關於愛、恩典與救贖的史詩,是靈魂的波瀾壯闊,是世上最偉大的「佈道」小說。
此篇小說最早的創作靈感,是雨果緣於1801年在法國發生的一件真實故事。一位叫彼埃爾•莫的農民,因為饑餓偷了一塊麫包,被判五年苦役。出獄後那張如影隨形的苦役犯的身份證,仿佛永久烙身的該隱記號,使他被整個社會拋棄。
倘若故事就此打住,僅僅譴責人間社會司法不公,那麼《悲慘世界》將是一部描摹外部人生困難狹窄的作品。如果苦難只為控訴和仇恨,那又怎麼配得起苦難的意義?偉大的巨著需要救贖的力量,需要找到真正的出路。
《悲慘世界》小說開篇描述著阿爾卑斯山的夜風,怎樣刺過衣褲的破洞,伴著絕望從四面八方襲擊著冉阿讓。他剛從關了他十九年的大牢裡假釋出獄,肩扛布袋、手提粗棍,靈魂在痛苦與仇恨中翻滾煎熬。在黑夜走投無路的情形下,他疑惑地敲開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門。
無條件的接納
卞福汝主教在教堂的居所裡無條件的接納了他。他對冉阿讓說:「您不用對我說您是誰。這並不是我的房子,這是耶穌基督的房子。這扇門並不問走進來的人有沒有名字,卻要問他有沒有痛苦。您有痛苦,您又餓又渴,您就安心待下吧。並且不應當謝我,不應當說我把您留在我的家裡。您是過路的人,我告訴您,與其說我是在我的家裡,倒不如說您是在您的家裡。這兒所有的東西都是您的。我為什麼要知道您的名字呢?並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訴我以前,您已經有了一個名字,是我早知道了的……您的名字叫『我的兄弟』。」
踏上救贖之路
從此,苦役犯冉阿讓在基督裡,一生的救贖之路開始了。
當然,救贖必需要付上贖價。在雨果救恩的神學裡,這一點他很清楚。
他踏過一切苦難的歷程,他用寬容來容納冤屈,他沒有讓靈魂幽暗珍珠似的淚水溢出眼眶。
重獲新生的冉阿讓從警官沙威的手中,贖出了被補的妓女芳汀。接著他又為了芳汀,從貪婪的酒店老闆夫婦手裡,用重價買回了她的女兒柯賽特。這其間,他又為了救出一個被誤判,為他頂罪的無辜人,他挺身而出,到案自首。為此,他付上救贖路上世人眼中最重的代價:他的市長身份,他的工廠資產,他受人尊敬的所有頭銜。為此,他重新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,但為了救人,他全部付出去了。
冉阿讓的生命裡,有一個一直在追捕他的警官沙威,而且日以繼夜,沒有休止。但冉阿讓最後不計前嫌,救出被起義群眾逮捕的沙威,他希望沙威能經歷重生的恩典,如同多年前,主教把恩典帶進他封閉的生命裡,使他重獲新生。可嘆的是,面對恩典的邀請,沙威雖然良心發現,放走了下水道裡爬出來的冉阿讓,但他最終自己拒絕了救贖。他想抓住恩典,卻為人間的律法堕落。他不知道真正的道義、律法在誰手裡。他只能最後在黑暗冷峻的星空下,凝視著一片混沌,在無法掌控的旋渦中,逃離這個世界,跳進了急流中的塞納河。
衰老、逃亡、勞瘁,這些要不了堅強的冉阿讓的命,但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兒柯賽特被人奪走的痛苦,才讓冉阿讓受了致命的傷。被冉阿讓救出的馬里斯,在和柯賽特結婚後的第二天,當他從冉阿讓口中,得知他身為苦役犯的身世之後,內心對他產生了疏遠和懷疑,從而阻斷了冉阿讓與柯賽特相見的各種機會。冉阿讓在黑暗淒涼的思念中,漸漸走向了死亡。
飲盡苦汁的生命
儘管最後,當馬里斯得知了真相,帶著柯賽特來到冉阿讓面前懺悔。然而臨終之際,冉阿讓並沒有譴責馬里斯。冉阿讓為了愛,諒解了他,寬恕了他,祝福了他。他將從主教那裡繼承來的燭臺交給了馬里斯,以自己飲盡苦汁的生命教導了他什麼是寬容和救贖。
小說最後,當女僕問只有一口氣的冉阿讓:「您需要一位神父嗎?」冉阿讓盯著某個虛空,他看見了基督仁慈的笑容,於是回答道:「不,我已經有了一位了。」
說著…說著……我眼中的淚水禁不住的簌簌而下,就像當初閱讀時,最後合上《悲慘世界》一樣。
人類的心有兩個心房,一個心房住著上帝,一個住著魔鬼。如果沒有永久的磐石,那麼永遠就會在撕裂,得不到安息。
正如雨果在小說中寫道:
「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,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,光明和黑暗交織著,廝殺著,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般無奈的人世間。」
Vivian聽得入了神,但我知道她還沒有聽懂。一個十四歲的少女,她還不懂人的內心既有來自上帝光亮的善,也有撒旦的罪性和黑暗滋生的惡。她還不明白世世代代作為我們的居所在哪裡。她還不知道什麼是「如此悲慘,天可憐見?」
但她已經擡起了頭,向著雨中的天空默禱。
地面街燈的影子閃爍。雨,飄落在街邊窗臺的玫瑰花上,像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紅寶石。碧綠的梧桐葉上,泛著神聖的銀光。而前方塞納河上,那朦朧的夜色,如煙如夢。
「走,我帶你去雨果家,再和你說說雨果吧。」
我拉著她的手,向著巴黎最美麗的廣場——孚日廣場走去。